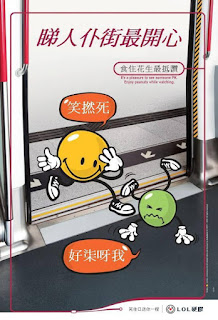粵語「攰」字,意思是「累」,這個字是否粗鄙不文呢?因為一開始我以為「攰」字只是個口語詞,於經傳無考,以致我忽略這個字的文化底蘊。其實這個字,最早見於《三國志.魏志.蔣濟傳》。當時賦役繁重,所以蔣濟上疏說:「弊攰之民,儻有水旱,百萬之衆,不為國用。」大意是說如果民眾極度疲累,再加上水旱,就算有一百萬人之多,也不能化為國家的力量。《康熙字典》引《集韻》的釋義是「疲極也」,不過《說文》無收「攰」字,「攰」字的語源是否就停在《三國志》呢?其實不然,「攰」是個後起字,只要找到較原始的寫法,就可以再往上推,找到更古老文獻中的用法。
一,「攰」字語源考
「攰」字讀音,據《康熙字典》引《集韻》為「居僞切」,折合《廣韻》音韻為「見母寘B韻三等合口」,即《廣韻》「䞈」小韻。「䞈」小韻下有「㩻」字(一個「小韻」內都是中古音中的同音字),釋義為「瘦極」。為何「攰」有「疲極也」之義,「㩻」有「瘦極」之義呢?我認為這和「攰」的本義有關,「攰」的本義應該是「斜」,由於人累到極點就依在牆邊休息,所以由「斜」義引伸出「疲極也」之義。由於「疲極」人就瘦弱,所以又引伸出「瘦極」之義。「攰」的「疲極也」之義可以引用《三國志》為證,「㩻」字的「瘦極」義我暫時找不到,不妨存疑。或許「瘦極」是「疲極」之訛,則和「攰」之「疲極也」同義。
好在《說文》有收「㩻」字,釋義為「㩻䧢」,等同後世的「崎嶇」,「崎嶇」就是不「不平」,凡是「打斜」之物則不平。《周禮》「去其淫怠與其奇邪之民」,段氏認為當中的「奇」字假借為「㩻」。[注一]鄭玄《注》:「奇邪,譎觚非常。」「譎觚」大概就是狡猾的意思。「奇邪」二字平列,「邪」即「斜」字,可見「奇」字也有「打斜」的意思。
凡物不正就有「邪」義,所以「奇」由「打斜」之義引伸出「譎觚狡猾」(狡猾)的意思,這是「奇」字語義引伸的第一個分支。「奇」即「㩻」字,所以「㩻」的本義為「打斜」、「不平」;「㩻」又引伸出「疲極也」之義,這個義項後世寫成「攰」,這是「奇」字語義引伸的第二個分支。
二,「攰」字時代考
《三國志》雖是晉朝陳壽所撰,不等如蔣濟或陳壽之時就有「攰」字,「攰」字或許是出於後世改寫。按版本來看,以上引用的百衲本《三國志》是「宋紹熙刻本原缺魏志三卷以宋紹興刻本配補」,所以南宋已經有「攰」字。
而《顏氏家訓》也有談論過「攰」字,有人問顏之推《三國志》上的「攰」是何字。[注二]作者顏之推是南朝梁至隋朝間人,所以「攰」字就可以上推至南北朝末期。假如認為上文「攰」字再上推至「㩻」「奇」二字過於曲折的話,至少可以相信顏之推的記載。顏之推明確記載他看到的《三國志》中的「攰」的確從支從力,所以最遲大約南北朝末期已經有「攰」字。
三,「攰」字音證
「攰」字讀音為「居僞切」,「僞」字為「寘B韻三等合口」,而「居」是見母字,切音等於《廣韻》「見母寘B韻三等合口」,即《廣韻》「䞈」小韻。《廣韻》「䞈」小韻下有「㩻」字。既然「攰」「㩻」二字中古音同音,語源可能一樣。「攰」的「疲極」義,及「㩻」的「瘦極」(或為「疲極」之訛),語源應該都是來自「奇」字,
「奇」字讀音為「見母支B韻三等開口」,「攰」字「見母寘B韻三等合口」,「寘B韻」即「支B韻」之去聲,「奇」是開口字,「攰」是合口字,只有介音不同,或許能夠音近互通?
攰,居僞切,「攰」字有合口介音,且保留在粵語中,而切下字「僞」字的介音在粵語中失落了,所以單用切語不能切出粵語讀音。從切上字及「僞」有介音,得知粵語聲母為kw。「寘B韻」字,通常變成粵語韻母/i/,如「智」字;/i/如果不能和聲母相配的話,就變成/ɐi/,如「為」字;或變成/ei/,如「戲」字。由於/i/和聲母kw能夠相配,所以推導出的粵語讀音是/kwi/陰去聲。粵語口語的「攰」字為/kwi/陽去聲,或許是古代「攰」字有清濁二讀,而古代韻書失收濁音一讀,而粵語保留濁音一讀,變成粵語的陽去聲。
四,注釋
[注一]《段注》:「廣韻云。㩻者、不正也。䧢者、䧢隅不安皃。俗用﨑嶇字、正此二字。㩻爲不正。故箸之訓曰飯㩻。言㩻衺之以入飯於口中也。」
[注二]《顏氏家訓.書證》:『有人訪吾曰:「魏志蔣濟上書云『弊攰之民』,是何字也?」余應之曰:「意為攰即是[危皮]倦之[危皮]耳。張揖、呂忱並云:『支傍作刀劍之刀,亦是剞字。』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,或借剞字,終當音九偽反。」』
按:[危皮]應作㩻,蓋形近而訛。「九偽反」和《康熙字典》引《集韻》之「居僞切」同音。
(百衲本《三國志.魏志.蔣濟傳》)
一,「攰」字語源考
「攰」字讀音,據《康熙字典》引《集韻》為「居僞切」,折合《廣韻》音韻為「見母寘B韻三等合口」,即《廣韻》「䞈」小韻。「䞈」小韻下有「㩻」字(一個「小韻」內都是中古音中的同音字),釋義為「瘦極」。為何「攰」有「疲極也」之義,「㩻」有「瘦極」之義呢?我認為這和「攰」的本義有關,「攰」的本義應該是「斜」,由於人累到極點就依在牆邊休息,所以由「斜」義引伸出「疲極也」之義。由於「疲極」人就瘦弱,所以又引伸出「瘦極」之義。「攰」的「疲極也」之義可以引用《三國志》為證,「㩻」字的「瘦極」義我暫時找不到,不妨存疑。或許「瘦極」是「疲極」之訛,則和「攰」之「疲極也」同義。
(士禮居黃氏叢書《周禮.天官冢宰.宮正》及《鄭注》)
好在《說文》有收「㩻」字,釋義為「㩻䧢」,等同後世的「崎嶇」,「崎嶇」就是不「不平」,凡是「打斜」之物則不平。《周禮》「去其淫怠與其奇邪之民」,段氏認為當中的「奇」字假借為「㩻」。[注一]鄭玄《注》:「奇邪,譎觚非常。」「譎觚」大概就是狡猾的意思。「奇邪」二字平列,「邪」即「斜」字,可見「奇」字也有「打斜」的意思。
凡物不正就有「邪」義,所以「奇」由「打斜」之義引伸出「譎觚狡猾」(狡猾)的意思,這是「奇」字語義引伸的第一個分支。「奇」即「㩻」字,所以「㩻」的本義為「打斜」、「不平」;「㩻」又引伸出「疲極也」之義,這個義項後世寫成「攰」,這是「奇」字語義引伸的第二個分支。
二,「攰」字時代考
《三國志》雖是晉朝陳壽所撰,不等如蔣濟或陳壽之時就有「攰」字,「攰」字或許是出於後世改寫。按版本來看,以上引用的百衲本《三國志》是「宋紹熙刻本原缺魏志三卷以宋紹興刻本配補」,所以南宋已經有「攰」字。
(四部叢刊初編《顏氏家訓.書證》)
而《顏氏家訓》也有談論過「攰」字,有人問顏之推《三國志》上的「攰」是何字。[注二]作者顏之推是南朝梁至隋朝間人,所以「攰」字就可以上推至南北朝末期。假如認為上文「攰」字再上推至「㩻」「奇」二字過於曲折的話,至少可以相信顏之推的記載。顏之推明確記載他看到的《三國志》中的「攰」的確從支從力,所以最遲大約南北朝末期已經有「攰」字。
三,「攰」字音證
「攰」字讀音為「居僞切」,「僞」字為「寘B韻三等合口」,而「居」是見母字,切音等於《廣韻》「見母寘B韻三等合口」,即《廣韻》「䞈」小韻。《廣韻》「䞈」小韻下有「㩻」字。既然「攰」「㩻」二字中古音同音,語源可能一樣。「攰」的「疲極」義,及「㩻」的「瘦極」(或為「疲極」之訛),語源應該都是來自「奇」字,
「奇」字讀音為「見母支B韻三等開口」,「攰」字「見母寘B韻三等合口」,「寘B韻」即「支B韻」之去聲,「奇」是開口字,「攰」是合口字,只有介音不同,或許能夠音近互通?
攰,居僞切,「攰」字有合口介音,且保留在粵語中,而切下字「僞」字的介音在粵語中失落了,所以單用切語不能切出粵語讀音。從切上字及「僞」有介音,得知粵語聲母為kw。「寘B韻」字,通常變成粵語韻母/i/,如「智」字;/i/如果不能和聲母相配的話,就變成/ɐi/,如「為」字;或變成/ei/,如「戲」字。由於/i/和聲母kw能夠相配,所以推導出的粵語讀音是/kwi/陰去聲。粵語口語的「攰」字為/kwi/陽去聲,或許是古代「攰」字有清濁二讀,而古代韻書失收濁音一讀,而粵語保留濁音一讀,變成粵語的陽去聲。
四,注釋
[注一]《段注》:「廣韻云。㩻者、不正也。䧢者、䧢隅不安皃。俗用﨑嶇字、正此二字。㩻爲不正。故箸之訓曰飯㩻。言㩻衺之以入飯於口中也。」
[注二]《顏氏家訓.書證》:『有人訪吾曰:「魏志蔣濟上書云『弊攰之民』,是何字也?」余應之曰:「意為攰即是[危皮]倦之[危皮]耳。張揖、呂忱並云:『支傍作刀劍之刀,亦是剞字。』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,或借剞字,終當音九偽反。」』
按:[危皮]應作㩻,蓋形近而訛。「九偽反」和《康熙字典》引《集韻》之「居僞切」同音。
(photo via fiker user qJake)